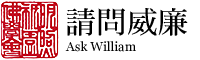父親的笑 ~~~聖嚴法師 民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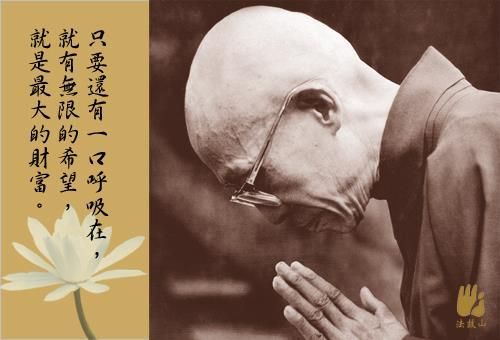
父親的笑 ~~~聖嚴法師
民國三十二年(西元一九四三年)冬天,我的母親不放心我在山上的生活,特地過江上山來看了我一次,相別僅僅數月,母親見我長高了好多,面色也白胖了一些,這才放了心,她在山頂上住了一夜,第二天就下山了。
大致上說,我能從鄉下人家的茅草屋裡,來到聞名於長江南北的狼山出家,她是滿意的;但是山上的生活,吃的方面,卻出乎她的意料之外,在她以為,狼山還是以前那樣的「錢山」,「錢山」上的和尚,是不應該吃得這樣差的。自然,我的俗家的生活,並不比狼山更好,其實是更差。所以我的母親是笑著下山的,因為她是小腳,我送她下山,一直送到離開狼山很遠,我才回頭。
民國三十三年(西元一九四四年)夏天,我曾回江南的俗家一
次。那時我回去,父母親對我似乎頗感失望,因我仍然穿著上山去時的衣服,那是我母親在兩年以前給我用粗布做的,此時,雖然未破,但已顯得舊了。我出家了一年,狼山的師長並未給我做一件衣服,即使後來,直到我離開狼山,到了上海,趕經懺,進了佛學院,也未給我做過一件新衣服。
一則,這時的狼山窮了;二則,狼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:小和尚未改裝,固然是穿俗家的衣服,小和尚落髮改裝時,也應由俗家做了全套的僧裝為小和尚的落髮而恭賀,並且還要俗家拿錢出來辦素筵供養師長,大宴親友,這一規矩是很有意義的,今日的泰緬等國,俗人出家,也都有著這樣的風尚。可惜以我那個貧窮的俗家而言,豈能如此的作法呢?我把這個規矩告訴了母親,她還為我難過了很久,她是怎麼也不會想到,送一個兒子做和尚,也像嫁女兒要陪上這樣大的本錢。
那次我回俗家,只住了三天,但我覺得俗家的事物和環境,樣樣都是值得留戀的。我在小時頑皮種下的幾株小樹苗,這時已比我的人還高了,有的已經開了花結了果,小時候二哥為我做的兩艘玩具木船,還靜悄悄地躺在屋角落裡;我讀過的書籍,還被母親包得整整齊齊地擺在衣櫥頂上;我的鉛筆、鉛筆刀、玻璃彈子以及貝殼小皮球等,都被母親收藏得好好的,似乎還在等著我回去。
從這些事物的保存,可以看出母親對於我懷念的深切。所以她要這樣對我說了:「你為什麼只請三天假呢?過去,當你倔強淘氣不聽話的時候,我真恨不得把你送掉,但在你上了狼山之後,身邊又像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似地感到不慣;想來想去,你總算是你們兄弟之中比較乖的一個。最難得的,是你自己知道讀書,也肯讀書,不像你的大哥,那時在江北,家裡有錢送他去
讀書,他卻寧可跟著野孩子們拾狗屎,說什麼也不肯上學,好像學堂裡的先生是老虎。唉!你呢?情形恰恰相反,我們做爹娘的竟又無力栽培你。」
說良心話,我的父母讓我去狼山出家,並不是由於佛法的理由,鄉下人根本就沒有聽過半句佛法,那能懂得什麼是出家的勝義呢?僅知道狼山是個錢山,狼山的和尚是財神,所以,送兒子去狼山出家,就等於送兒子去登天享福。雖然如此,母親也是在半肯半不肯的心情下,甚至可說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景下把我送出家門的。
當時我才是個十五歲的大孩子,在俗家住了三天,真想再住幾天,陪陪母親,尤其在那年的春天,我的二姊因為難產而新死不久,母親感到特別的傷痛,她每天都會泣不成聲地提到我的二姊。母親的確是要悲傷的,到了晚年來臨時,最小的兒子出了家,等於死了一半,最小的女兒,又不幸早亡!
但是,狼山的規矩,小和尚一年只准回俗家一次,每次三天假,因我的俗家住在江南,來回的水陸路程就去了兩天,所以,連頭帶尾准了我五天假。如果逾假不歸,雖不致發生什麼嚴重的問題,但那總是給了師長們一個不好的印象。出家人不該顧俗家,狼山也最忌諱子孫顧俗家,所以,小和尚如果沒有事,最好不要回俗家。
俗家是回不得的,然而,小和尚的服裝,仍得由俗家來負擔。民國三十五年(西元一九四六年)春天,我在上海的下院,已經正式趕經懺了,穿著俗服,披上水紅色的麻布七衣,雜在師父們之中,天天出堂做佛事,齋主人家知道我是小和尚,倒也很少計較,我的曾師祖──下院的當家,卻覺得看不順眼,所以念著要我改裝,但又捨不得為我花錢剪布。我是聽在耳裡,難過在心裡,出家已經兩年多了,還沒有穿上僧服,自己何嘗不急?
終於,我的父親冒著斷糧挨餓的勇氣,賣掉了幾擔麥子,請鄉下的土裁縫,做了幾件僧裝的棉衣,親自送到上海。父親還對我抱歉似地說:「你們的娘,眼力不行了,她也不會裁剪和尚衣,請了裁縫,嘴上雖說會做,做得卻不像樣,布料也很差。這些年來,鄉下一直在亂,粗重的活計,我已做不動了,你的哥哥嫂嫂,自顧生活不暇,所以也幫不上手腳。唉!這些衣服,
我雖送了上來,但還不知道你敢不敢穿了它們在上海見人。不管怎樣,你且穿著試試,看看合不合身?」
我是照著父親的意思做了。滿意,當然是說不上的,但是畢竟是父母的血汗、父母的心呀!父親見我歡天喜地,他也開心地笑了,這一笑,似乎就已值回了他全部心血的代價!
就這樣,我就算是改裝了,反正俗家沒有錢,所以,一切的儀式也都免了。我的狼山的師長們,不太重視律制,似乎也缺少了一些人間應有的溫情。也許是由於生活艱難與時局動亂的緣故罷!所以,我也並不埋怨什麼人,如要埋怨,應該是埋怨自己的福薄。
噩耗
我出家之後,直到如今,一共回了三次俗家。第一次,就是民國三十三年(西元一九四四年)的夏天。第二次,是在民國三十四年(西元一九四五年)的秋天。第三次,是在民國三十七年(西元一九四八年)的秋天,那時候,我已離開了小廟,已經進了上海靜安寺的佛學院。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回俗家。那次,因為我的母親病危,特別派我的三哥到上海接我。那次,我是在氣急敗壞的情況下,向學院裡請准了假,跟著我的三哥連夜趕回鄉下去的。
我們乘的是火車,那是我第一次乘坐了京滬線上的火車,坐了三等車廂的夜班車,從北站乘到無錫,下了車等了三、四個小時,才天亮。我的三哥,在鄉下是蠻靈活的,到了上海,竟顯得土頭土腦,那副鄉巴佬的神情,卻又處處為我著想,把我當作公子哥兒,他自己好像是個跟包的聽差,在他以為,在上海念佛學院的「小老爺」,一定不能像小時候那樣地經得起折磨了。買了三等車廂的車票,他老覺得對我不起似地,上車之後,到處為我找座位,但是,車廂裡早已擠滿了,跑車幫的男男女女、綑綑包
包、籮籮筐筐,以及一些苦力和軍人,又到那兒去找座位呢?他從頭一節車廂擠到末一節車廂,也沒有找到一個空位。最後,還是一位好心的軍官,給我讓出了半個位子。至於我的三哥,他就坐在那位軍官的行李上面,那位軍官,真是一位好心的人。
從無錫換乘內港航行的「小火輪」,秋季的內港水路很淺,水底到處長著像孔雀尾似的水草,汽艇的葉槳,不時地跟水草糾纏,航行了一程,必須停下來清理一次。內港的兩岸都很高,港面不太寬,秋天的太陽又是有名的秋老虎!就這樣行行又停停地航了一整天,受了一天的罪,到天黑之後,才算航到了不能再向前航的地方下了船。
我和三哥抵達家門的時候,已是午夜時分了。俗家的四周,除了唧唧的蟲聲,靜得幾乎使我感到恐怖,但也沒有什麼不幸的跡象可以看到。三哥要我放開嗓子叫門,好讓父母高興一下,我就照著做了:「阿爸,開門哪,我和小阿哥回來啦!」
屋裡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一絲動靜。當我喊了三聲之後,父親才應聲出來。父親把昏黃的油燈撥亮,他顯得很疲乏、很蒼老,帶著憂慮而又欣慰的表情對我說:「你們的娘已盼望好幾天了,這幾天,天天都在念著你,她說今晚,你一定能夠到家的,所以一直沒有睡著,剛才我還沒有聽到叫門,倒是你們的娘把我推醒了。」
阿彌陀佛,感謝佛菩薩的保佑,母親尚能見到我哩!我聽完父親的話,心上的一塊石頭,總算放了下來。
當我迫不及待地走到母親的床前,我還沒有開口,倒是母親先喊了我的名字。她的神情,顯得很愉快,雖然一個像小山似的大肚皮襯托出那張焦黃而乾癟的臉龐,看來令人心酸。
「不要緊的,我的病,前天有人送來一張專治水腫的祕方,吃了些時日就會好的,今天我也覺得舒暢了一些,精神也好了一些,要是一直像三天以前那樣,恐怕今天我已見不到你了。」
我尚沒有想到應該用怎樣的話來慰問母親,倒被母親首先安慰了一番。我正想說一句什麼話的時候,母親又接著往下說了:「早曉得如此,你小阿哥的這一趟上海,也是多跑的,害得你急急忙忙地趕了回來。其實嘛,生病等於享福,我一生難得休息十天半月的,這一來,我倒可以安安靜靜地什麼事也不用去做了。唉!只是辛苦了你們的爹,裡裡外外,都由他去張羅,前幾天我病重的時候,一連幾天幾夜,他都沒有閤一閤眼,要是我再不好,只怕也要把他累倒了!」
聽到這裡,我真想放聲大哭,我還能說什麼呢?俗說:「養兒防老,積穀防饑。」當父母老病了的時候,我們做兒女的,竟然不曾發生絲毫的作用!父母時時為兒女著想,處處替兒女打算,做兒女的又為父母著想了多少,為父母打算了多少?母親到了這樣病重的時候,始終沒有為自己擔憂,倒是體惜她的兒女、體惜兒女的父親。
母親見我在暗暗地飲泣,於是,她的語調,放得更加平靜、更加慈祥了:「你難過什麼呢?你姆媽不是還在好好地和你說話嗎?你回來了,我比什麼都高興,你比幾年以前長高多了,今天夜深了,你們兄弟倆在路上也很辛苦了,到明天,再讓我仔細地看看你。不要哭,又不是十歲、八歲的小孩子,見了久別重逢的姆媽,還要訴苦嗎?」
經過母親這麼一說,我倒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,一個出家數年的人,感情還會如此的脆弱。可是,直到現在,回憶起當時的情景,仍不免要淚眼模糊地俯首啜泣!
的確,我的回家,對於母親的病,很有幫助。我天天陪伴著母親,許多的事,母親都希望我替她做。母親有著說不完的話要對我說,每次說了幾句又不往下說了,似乎,由於我的出家,已使母子之間隔了一道牆壁。但她告訴我一些有關我童年的往事,聽了那些非常可笑的事,我笑,她也笑。
我勸她念佛,她說她已念了很久了。她對我的一串玻璃念珠很喜歡,拿在手上不停地數,可惜那是我向監學守成法師借的,回上海時又向母親要了過來,沒有能送給她。她的睡眠增加了,飲食也增加了,有時也能勉強著坐起來了。她看看自己的大肚皮,往往會從嘴角上泛起一絲苦笑,因為她也知道,凡是害上了這樣的病,在一個鄉下的窮人來說,痊癒的機會根本是非常的稀少,什麼藥物、什麼祕方,頂多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。
同時,母親也很相信「藥能醫病,不能醫命」。所以她也坦然地對我說:「今年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了,你們兄弟姊妹也不用照應了,能趕在你們爹的前面先走一步,倒是我的福氣。……」說到這裡,她便曳然而止,不再往下說了。但我已經聽出她的弦外之音,那就是養兒育女不中用,老倆口子還得相依為命,如果晚走了一步,臥病之後,又有誰來悉心地照顧?
我是不用說了,我的三個哥哥,老大、老二,都已分開來住,老三雖跟父母住在一塊,也有妻子的生活負擔,一天不做一天不能生活。縱有孝子,豈有老伴那樣地體貼。父母看兒女是肉裡的肉,兒女看父母是皮外的皮,雖然是一樣的痛,痛的程度卻不同!我的母親,豈不是已經體驗到了這一層道理?
我不是善於流淚的人,當我想到這裡,竟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!我雖希望在家裡多住一些日子,我的身分、我的學業、我的假期,卻要把我從母親的身旁拉走。在家伴著母親住了半個月,母親的病況,沒有惡化,心情雖較開朗,但也沒有痊癒的跡象。
我是不能再住下去了。母親也天天問我為什麼還不走?她是不希望我走的,卻又硬要趕我走;為她自己著想,為我前途著想,她是矛盾的、痛苦的。
終於,我是走了。終於,我也得到了喪母的噩耗!
那是過了兩個多月,接到了我二哥從他做工的紗廠打來的電話,那是上海小沙度路的一家拉絨廠,他說他與大哥、三哥,在農曆九月上旬,已經把母親的後事料理定當,請齋公做了一天「道場」,母親的靈柩,暫時葬在我家附近的租田上,三年以後,再將遺骨送到張氏祖宗的祖墳中去。他說,因為遵照母親的遺命,沒有通知我回鄉奔喪,一則顧慮我的學業,再則顧慮路上太亂。但我深深地抱怨,家裡為什麼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?
哀哀父母
母親對於我的照顧,一直到她死了之後,還在庇蔭著我,處處為我著想。至於我這個兒子呢?我竟想不出曾有過表示孝心的事。所謂「樹欲靜兮風不止,子欲養兮親不待」,母親沒有等待到我能夠有力奉養她的時候,她就去了!事實上,縱然她能一直等到現在,在現實的局勢下,我又有什麼辦法去奉養她呢?可憐,我連母親的忌日是那一天,都不知道啊!
民國三十七年(西元一九四八年)的冬季,學院放了寒假,我決心要回俗家走一趟,但是,當我乘火車到了無錫,因為新四軍的勢力已經到了我的家鄉,內港沒有船了,公路的汽車也不通行了,要是步行回去,第一路途不熟,第二危險很大,在百多里的旅途之中,隨時都可能遇到變故。不得已,只好折返了上海。
過了民國三十八年(西元一九四九年)的農曆新年,我俗家的人,多半都到了上海,他們是我的三個哥哥、兩個姊夫、一個嫂子、一個堂姊、一個表姊。鄉下鬧得天翻地覆,所以老百姓都活不成了,大家都來上海餬口了,家裡僅留下父親一個人。我問他們,父親的情況怎樣,他們只說老年人總比較好些,大概不會有危險,其餘的,他們也不得而知。他們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險,步行到上海的,從家鄉到上海,晝伏夜行,忍飢耐餓,費時半個多月,也是夠他們苦的了。
然而,當我要報名從軍的前夕,去曹家渡的一個亭子間裡看他們,他們又準備著步行還鄉了。這時的共軍已經控制江南的大局,並且已到了崑山。他們聽說對於自動還鄉的人一律寬恕,否則,等到迫令還鄉,性命就難保了。唯有一向在上海擺豆漿攤的大哥,他是聽天由命,不動聲色。因此,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,我俗家的人,又僅剩下我大哥一個人在上海了。我將部分東西裝了一箱,留在他那裡,並且請他代我向父親告假,說我已經去了臺灣、還了俗、當了兵,能否再有相見的機會,誰也不能預料,
請他老人家保重,也請幾位哥哥好好地孝養父親。
一晃之間,我來臺灣,已是十八年了,父親如尚健在,也該是七十八歲的人了。但願他老人家在三個哥哥的孝養中,晚景很好,過得很平安。然而,誰又能夠如此的肯定呢?何況,我的父親在他五十多歲以後,就已患了胃病!
我的父母雙親,現在何處呢?究竟怎樣了呢?父親的健康?母親的靈?
《詩經》的〈蓼莪篇〉說的:「哀哀父母」,我豈不就是那樣的人嗎?在生之時不能奉侍孝養,母親命終又不能奔喪。縱然那天是我父母的壽辰,我也不得而知呀!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?作為一個出家人,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,我唯有每天在佛前為父母的健康和超昇而祈禱。
在廣大的人海之中,我的父母實在算不得什麼,既無赫赫之名,也無什麼建樹,乃至連對子女的教育費用也籌措不出。但是,人間的安立,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,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?我的父母,乃是標準的普通人,是安分守己的平凡人物,沒有強烈的欲望,對於生活卻從不失望。
我曾聽父親常常勉勵我們兄弟:「一群鴨子在河裡游,各有一條路,大鴨游出大路,小鴨游出小路,不游就沒有路。但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,不要嫉妒他人,也勿輕視自己。」
有一次,幾位鄰婦和我母親聊天,忽然有人拿我來做評論的對象,有一位鄰婦把我預言得不能再好,另一位卻不以為然,她們最後的結語是在好壞兩可之間:「好則住在樓上樓,不好則在樓下為人搬磚頭。」我的母親這時也說話了:「樓上樓當然好,搬磚頭也不錯,只要他不做賊骨頭,我就放心了。」當時聽得大家哈哈一笑。
現在想來,父母的話著實夠我受用的了。